金庸、李詠和單田芳:不問江湖風波惡,歸去包不同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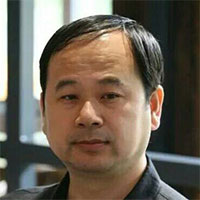
清晨,打開微信,突然看到好友群里的一幅字:先生已隨桃花去 世上再無俠客行。
當時,就是心頭一震:莫非金大俠……敢緊打開朋友圈,赫然N篇文章的標題都是在談武論道、說古論金。而且,就算是不點開這些文章,也可以猜到:金大俠真的已步單田芳先生、李詠老師后塵,鶴駕西游了。
所以,今天,不寫體育,也不聊戰(zhàn)斗的民族,只想說說金庸和他同在天堂的兩位同伴。
短短不到兩個月的時間,三位影響過上億人生活的媒體人,永遠地離開了“曾經(jīng)”或是“一直”熱愛著他們的聽眾、觀眾和讀者,當然,按時髦的話講,這些人是粉絲。
很感慨.因為,他們真的是三位媒體圈標志性的人物,標志了一份屬于他們自己、也屬于一個時代的輝煌。更因為,自己確曾見證了他們過往的那份輝煌。
金大俠和單先生,雖然一個是1924年生人,一個是1934年生人,但相對于他們在大陸的粉絲而言,也應當也算是同齡人了。因此,在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下,他們應當幾乎是同時進入粉絲視野的。而且,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,感覺身處香港的金大俠,其成為全中國風靡至極的偶像,較之年齡比他還小些的單先生,似乎還要晚些,當然,較之1969年出生的李老師,則要早上十多年了。不過,由于改革開放這一時代性的共同因素,他們成為偶像級的人物,前后也就是十來年的差距。所以,對于當今即使就算是才二十多歲的朋友而言,他們也都不會太過陌生。
單先生,作為音頻時代的標志性人物,應當是隨著改革開放的腳步進入中國公眾視野的。年輕時曾經(jīng)紅極一時的這位評書藝術(shù)家,快到五十歲的時候,再次成為了全中國家喻戶曉的人物。當然,他的作品能夠流傳起來,功勞應當屬于收音機這一改革開放后每家必備的傳播平臺。那會兒,現(xiàn)在家家閑著基本不用的電視,尚是普通家庭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。
記得,第一次聽單先生的評書,應當是八十年代初他每天中午13:00在廣播電臺上連播的《隋唐演義》。至今,三十多年過去了,偶爾和同齡人吹牛,能夠隨口說出隋唐十三條好漢的名字,仍然是我深以為榮的事情:畢竟,那代表了我無憂無慮但卻渴望知識的童年,要知道,上世紀七、八十年代,買書不僅是高雅的事情,更是需要資金的事情,所以,不用花費一分錢的小說評書連播,應當是普通孩子獲得是非觀和開闊眼界的最佳途徑。
評書對孩子們的影響是潤物細無聲的。所以,低我一屆的初中校友們,曾在學校后面的樹林里開了一個“村北小教場”:當班中有男生發(fā)生矛盾時,所有男同學會一起來到小教場,發(fā)生矛盾的兩個同學則當眾按規(guī)則比武開練——只許用拳頭而且不許攻擊致命部位亂打一氣!據(jù)說,這個“小教場”存在了好長一段時間,也解決了很多的事情。當然,其自然逃脫不了被老師發(fā)現(xiàn)并取締之命運的,但終究是留下了一個酒后用來打趣的傳說。
上了高中以及工作之后,由于學習和生活的節(jié)奏都大大加快了,就很少聽單先生的評書了。只不過,搭乘出租車時,偶爾聽到他那略帶滄桑的聲音之際,仍會倍感親切。如今,年齡漸長,偶爾身處異國他鄉(xiāng)、長夜難眠之際,手機放出來的單先生評書,還真是最好的催眠曲。
金大俠,作為報紙時代的標志性人物,應當也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步伐,先是在廣東成名,之后才逐漸滲透到內(nèi)地的:八十年代初,他的作品已在廣東結(jié)集出版的時候,北方的《武林》雜志還只是連載了其射雕三步曲中的一小段《黑風雙煞》。
記得,我就是在讀初中時,通過《武林》連載的《黑風雙煞》結(jié)緣金庸先生的,高中時則對他的書達到了癡迷的程度——馬上就要高考了,但還是忍不住連夜看完了他一部四冊的小說。現(xiàn)在的年輕人應當很難理解:三十年多年前,全中國的青少年們,怎會因為一本《射雕英雄傳》而如癡如醉?但那時,確實是一個女孩子讀瓊瑤、男孩子聊金庸的時代,就像是現(xiàn)在的女孩子玩抖音,男孩子玩快手一樣。所以,“飛雪連天射白鹿,笑書神俠倚碧鴛”這幅對聯(lián),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初期,絕對是眾多年輕人尋找江湖同道時必須面對的流行切口。
金大俠雖然是作家和報人,但由于他的作品多被影視所改編,因此,搭乘了視頻這一新傳播技術(shù)之后,金大俠也就和眾多明星演員一樣,成為了不僅自帶流量、還可以為他人帶來流量的話題性人物:不僅李敖大師生前曾在電視上公開指責他寫的東西什么也不是,就算是到了移動互聯(lián)時代的現(xiàn)在,仍然有人憑借在微信公眾號上玩“金學”而每每十萬+,而且,這十萬+,不僅指的是粉絲流,更是指的現(xiàn)金流。
李詠老師,應當屬于電視時代的標志性人物。如果說金大俠成名有借電視之力的成份,單先生也曾嘗試過電視評書但并不是那么成功,那么,李詠老師,則應當算是完全依靠電視做到舉國聞名的。
李詠老師,1968年生人,簡歷顯示,他是1987年考入的北廣——現(xiàn)在的中國傳媒大學。1985年前后的高考,絕對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。所以,那時候能夠讀到大學的人,是被稱為“天之驕子”的,是絕對有理想的一代人。所以,私下以為:經(jīng)過北廣這一著名文化學府的培育之后,有理想的李詠,應當是有濟世報國雄心的。
然而,李詠真正名揚天下,卻是以娛樂明星主持人的身份,就像是《開心辭典》中她的同齡人王小丫一樣,雖然有著滿腹才華和N多想說的話、想做的事,但卻要用最簡單粗暴的娛樂形式來實現(xiàn)最基本的傳播。
記得2005年前后,在飯局上,一位北廣的女研究生朋友曾聊到:上周,她心情不好,在長安街上漫無目的閑走,突然看到李詠的大奔飛駛而過,馬上就打電話吼了他一句:你在長安街上胡逛什么?!超速了沒有?!而且,聽到李詠驚訝的聲音之后,她馬上就掛斷了電話,根本沒給他判斷是誰打電話的機會!給我們講完這個故事,小姑娘哈哈大笑!相信,那天她和李詠玩過惡作劇之后,心情也是相當愉快的!
真的可以講,這位北廣的小研究生,那天就算是看到金大俠或是單先生從身邊走過,也不會和他們開玩笑調(diào)節(jié)心情的。也許,這就是李詠老師的悲哀之處:他在用自己的痛苦,帶給別人歡樂。就像是那些美國常青藤出來的工程師,天天要研究學渣們最喜歡玩的游戲。
也許,厭倦了娛樂背后的痛苦、更看清了主持人在電視這一傳播平臺的發(fā)展趨勢,2014年,在移動互聯(lián)時代到來之際,李詠老師離開光環(huán)滿滿的央視回到了母校任教,再次成為崔永元同事之際,相信他們應當也會探討“電視這種傳播手段是否已經(jīng)被手機威脅”這個跨時代的問題。
可惜,未及在高等學府里著作等身,更未及對新媒體發(fā)表宏論巨著,李詠老師英年早逝,雖給媒體圈也留下了一個事業(yè)及代價的思考,但這份思考的代價卻實在是太大, 只能是讓幾乎所有的人一聲嘆息。
嘆息之余,只能說,這時間過得真快:小時候真的很崇拜口吐蓮花的單先生,中學時很癡迷金大俠的江湖世界,大學剛畢業(yè)時則很欣賞李老師的特立獨行,但這一切,突然就都成為了過去。
現(xiàn)在想來,如果硬要站在傳播的角度觀察一下這三位前輩,感覺最為獨特的應當還是金大俠。這無關(guān)他們的學識水平,只是因為:金大俠的作品,不同的年齡會有不同的感覺,而且其還可以隨時拿出來閱讀理解,無論是在人來人往的車站中,還是在空無一人的公園里,一份成年人童話中快意恩仇的快樂馬上就會呈現(xiàn)在我們面前!而單先生和李老師的作品,要品味起來,對環(huán)境及心情的要求,就要復雜的多了。盡管,到了移動互聯(lián)時代,他們?nèi)蛔髌返某尸F(xiàn)方式,都是一樣的簡單。
今天,也許就是為了顯示自己多么卓然不群,有些人在重拾李敖的牙慧,高談闊論武俠小說這種大眾文化的膚淺。所以,忍不住寫了上面的這些文字,只想說明一個簡單至極的觀點:無論如何,金大俠的書,以及單先生的評書、李老師的節(jié)目,都起到了文化普及的作用。而且,這種普及,還真的不是娛樂至死式的聲色犬馬。
至于他們的影響力,也許,金大俠筆下兩個最為著名的悲劇性人物——少林寺玄慈方丈及華山寧中則女俠——都曾堅持的主張,應當是最好的注解:當少林寺和華山派面臨艱巨困難之際,他們都選擇了“盡人事、安天命”式的放手一搏!只要盡力了,就不要管結(jié)果了。
吟到恩仇心事涌,江湖俠骨已無多。但愿,這三位曾經(jīng)帶給我們快樂的大師,在天國遇到像李敖這樣的攻擊者,能夠相逢一筆泯恩仇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