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- 首頁
- >
- 正文
【深度】欠薪正在逐漸壓垮中國職業足球

體壇周報全媒體特約記者 冉雄飛
沒有規矩,不成方圓,中國足球職業化27年來依舊一地雞毛,可以歸根結底為沒有規矩。
規矩就是規則,職業足球的運作法則,可中國足球職業聯賽從1994年紅山口會議后入市到2021年遭遇全面饑荒,運作了26個賽季的職業足球依然在偽職業聯賽,俱樂部大面積欠薪,球員四處討債,罷訓罷賽,討薪無門,足協亂政,俱樂部生死存亡等一片亂象中艱難生存,歸根索源就是沒有立好規矩,定好規則。

職業足球的核心和重心是職業足球俱樂部,沒有職業俱樂部就沒有職業足球聯賽,但中國的職業足球俱樂部卻異常脆弱,生存困難,2020賽季之前,在中國足協登記在冊的22家職業俱樂部在短短一百天之內宣布破產,轉讓,解散或徹底退出,其中包括中超天津天海,4支中甲俱樂部,含十連冠的遼足,上海申鑫,四川隆發,廣東華南虎,7支中乙和12支中冠球隊。2021賽季還沒有開打,由于中國足協的“工資表”大限,中超俱樂部豪門和新科冠軍江蘇蘇寧,河北華夏幸福,重慶當代和天津泰達等四家頂級俱樂部面臨著“不交表,不準入”即退出中國職業足壇的巨大風險,中超俱樂部都如此這般,更別說生存更困難的中甲和中乙俱樂部。
數十家職業足球俱樂部為何面對著足協高舉的“準入大棒”生存或是毀滅?無外乎就是因為足協在陳戌源主席2019年下半年上任后推出的一系列新政和改革措施。足協改革的初衷是為了規范職業俱樂部的良性發展和規范化建設,但一張工資表就催生了22家職業俱樂部在2020賽季前的猝死,一個中性名稱的改革就導致俱樂部投資人熱情銳減,很多俱樂部沒有了背后的大金主,立馬就徹底陷入了經濟危機,瀕臨死亡。

2020年對于全世界的職業體育產業都是一個特殊的年份,可即使新冠病毒肆虐導致全球的職業體育俱樂部“關門閉戶營業”,歐洲的職業足球聯賽依然運作良好,頂級俱樂部的收入雖有減少,卻依舊能夠生存,據德勤足壇財富榜的最新數據,巴塞羅那俱樂部在2020賽季收入6.271億英鎊,英超的曼聯俱樂部收入5.09億英鎊,比去年少了1.18億,歐洲最賺錢和最大的前20家俱樂部在2020賽季整體收入減少了18億英鎊約合20億歐元。
反觀中國職業足球聯賽,由于疫情導致聯賽被迫采用賽會制方式舉行,所有俱樂部除了中國足協和職業聯盟的分紅收入,其他收入幾乎為零。1月28日足協提前給16家中超俱樂部分紅700萬人民幣,這筆錢只相當于90萬歐元,對于虧損巨大的職業俱樂部來說只是杯水車薪,而在2018賽季,中超俱樂部平均分紅7400萬,2019賽季分紅6000萬,今年最終能分多少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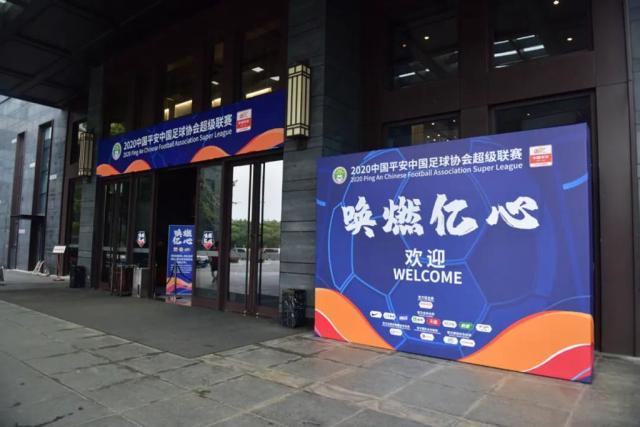
相對于歐洲頂級聯賽的收入結構,電視轉播權分紅,博彩業,比賽日收入,贊助商收入和授權產品銷售等,歐洲俱樂部收入相對更多元化,收入比重合理,導致俱樂部抗風險,抗壓能力較強,而中國國內職業俱樂部主要以“冠名權”為主的商業贊助作為盈利點, 絕大多數俱樂部依賴于俱樂部金主輸血為主,這部分收入占俱樂部總體收入的70%以上,一旦“冠名權”贊助資金不到位, 俱樂部就必然面臨嚴重的經濟危機,欠薪就成為必然。
中國足球職業化改革從1994年到2021年,始終都沒有解決俱樂部造血功能的問題,放眼全球的職業俱樂部,中國足壇盛行的一直是“高冠名權收入模式”,也就是說,推動中國職業足球改革的,是一個個帶著投資熱情和足球情懷的投資人。足協主席陳戌源在2019年上任后主導的一系列改革措施,比如工資表準入,俱樂部中性名改革等,從根本上是想解決俱樂部的健康和自身造血問題,但卻在特殊的年份動搖了職業足球俱樂部的根基,加速了職業俱樂部的死亡。

俱樂部欠薪在中國職業足壇是常態現象,職業化改革之初有,到現在為止依然無法根除,造血功能不足也是歷史原因,導致俱樂部不能健康發展是一個社會問題,不單純是俱樂部投資人投資足球動機不純的表面現象,在2020年經濟大環境如此惡劣的背景下,中國足協在2021賽季硬性一刀切推動職業俱樂部的中性名改革,是幫助俱樂部更好的生存呢?還是加速職業俱樂部的死亡?
從世界足球的角度來看,任何一個國家的官方足協都是三件事:國家隊建設,青訓體系和職業足球聯賽,世界足球強國西班牙,意大利,英格蘭,巴西等,都是把職業足球的運營和管理交給職業足球聯盟,官方足協的主要任務是抓國家隊建設和青訓,推動與發展足球人口,但中國足協推動職業化足球改革27年來,始終不愿意真正放手,一方面是國家隊成績的劇烈動蕩和青訓體系的崩塌,另一方面則是職業足球聯賽假賭黑盛行,俱樂部收入不穩定卻負擔很重,甚至是不堪重負,以前是管辦不分,一套班子,兩塊牌子,現在是職業聯盟依然在中國足協的強力操控之下,分而不離,假如這兩個賽季的改革是在職業聯盟的主導之下,全體職業俱樂部共同商議決策而出,會導致俱樂部大面積死亡嗎?

中國足協主導的職業化改革,多年來最被詬病的就是缺乏長遠規劃,缺乏穩定性和持續性,頭疼治頭,腳痛醫腳,規矩不存,何來規則?比如限薪令,2020賽季要求地是職業球員本土球員頂薪1000萬,國腳1200萬,2021年馬上又要求頂薪稅前最高五百萬,外援最高300萬歐元,如此翻手為云,覆手為雨,直接導致了球員和俱樂部的利益沖突甚至對立,俱樂部何去何從?球員如何信服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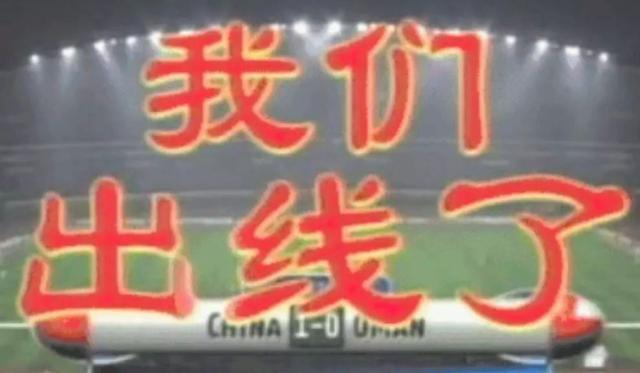
足球職業化改革27年以來,足協新政,懶政,勤政和亂政成為了一條發展主線,王俊生時代借改革春風,一系列職業化新政造就了甲A時代的輝煌,中國男足也在2001年歷史性的沖擊世界杯成功;閆世鐸和謝亞龍時代可以說是亂政不斷,女足各種折騰,職業聯賽停止升降級,為世界杯讓路,為奧運會騰道兒,最終卻是05,09,13年三次世界杯小組賽失利,08年奧運會男女足全面丟人;張劍時代可以說是懶政,但無為而治也并非無功,廣州恒大強勢進入中國足壇,兩屆亞冠冠軍,中超7連冠,一時間金元足球橫行,俱樂部投資規模驟增,但虧損也巨大;陳戌源主席上任這兩年,看上去是勤政為民,可也有亂政的嫌疑,工資表準入導致職業俱樂部大面積死亡,俱樂部中性名改革導致投資人熱情下降,資本大量撤離,勤政是不是也有些矯枉過正,過猶不及呢?

俱樂部欠薪是中國職業足球發展的歷史遺留問題,不根本解決中國職業俱樂部的收入結構不合理,單純依賴輸血的本源性問題,俱樂部欠薪依舊會持續下去,只是2020年這個特殊的年份會變得更嚴重而已。從這個角度來說,中國足協目前推動的職業俱樂部改革,還是應該以“穩定壓倒一切”的大格局出發,先幫助與保證職業俱樂部在2021年先活著,而不是黑面無私地一刀切下去,真要像2020年一下子干死22家職業足球俱樂部,毛之不存,皮將焉附?

















